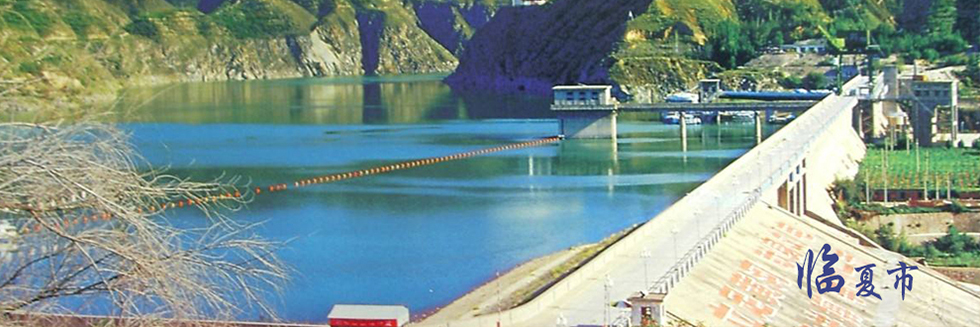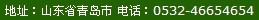|
作者简介 赵君平,甘肃省西和县人,80后文学爱好者。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有作品在《中国散文家》《华夏散文》《飞天》《秦都》等刊发表。 1在云台,择一地,与君采桑耕田 来到康北的时候,恰逢“大暑”,满目的苍翠被点燃了,涓涓的河流被点燃了,康北的风也被点燃了。火一样的康北,将我们夹裹其中。怀揣着火一样的激情,我们在康北行走,奔赴一场流火的“文字之约”。云台山,在想象里,我把他理解成云的歇台,山上盛开着大多雪白的云彩,是康北纤尘不染的诗行。据说民国14年在云台山修建一座寺庙,朝山者常年络绎不绝,香火极盛,远近闻名,因此,让白马关改了姓名:云台。白马关成了云台的乳名。我们没有去云台山,没有见到庙,也没有见到修行者。无法想象百年前人们登临云台山,人潮涌动的场景。山不在高,有仙则名,云台山是该有座庙的。好让登攀的人,有个念想,有个朝拜的神,可以让云台山的香火,云台山的云海被更多的人分享。在云台镇我们去了梧桐,大山岔,毛娅山观景台,白马关东城楼。到毛娅山观景台时,已经10点左右,一望无垠的蓝天,阳光耀眼。在观景台,背靠着栏杆,将头昂起,看流云,似乎在脸上拂过,有点晕,晕云的感觉,很微妙。悄悄闭上眼睛,在这种极度眩晕的状态中缓冲一会。然后,俯下身子,看连绵不断的群山,宛如一个大棋盘上的棋子,错落有致的小路就是不规则的楚河汉界。这盘棋不知是谁布的局,不知道要等谁来下?一定有高人在此盘踞。冷硬的水泥公路上,种着一排排柔情的“迎客竹”。那些清秀的竹子,踩着高山,挽着流云,是康北路上最美丽的点缀。此刻,毛娅山的一草一木在阳光打下的光影里,安静的洗着日光浴,神采奕奕。而山脚下星罗密布的房子,此刻也醉在阳光里。我们不如一棵草,受不了阳光如此热烈厚重的爱,个个汗流浃背,一下车全往阴凉的地方躲。在一块大石头上,刻着“美丽大堡”四个字,很醒目,意思也很直白明了。围着石头拍照,忽然发现旁边的石头上,刻着“万家大梁云海东岳泰山玄机”几个字,倒是很有意思。也许这才是一副联,而那美丽大堡四字,无非是楹联而已。康北的山,山大林密,水草丰茂,像康北的男人,豪放。而类似云台“大水沟”这样的溪水流泉,就是康北的女人,灵性十足而且泼辣能干。这时候,在山里劳动的人,唱着山歌解渴。不信你听:清早起来钻进沟,一泉凉水清溜溜。凉水不是多喝的,留下六月解渴的。凉水能解心中火,贤妹能解小哥哥。凉水不喝淌着来,贤妹人小长着来。一朝长成七仙女,一顶花轿抬回你。我们一路说笑着,一路就到了蚕桑基地。据邓文德主任介绍,这里以后将会开发成为甘肃最大的蚕桑基地。无限广阔的前景画卷一样徐徐展开。在茶马古道上,有这么一处地,也是有文化内涵的景点。脑海中浮现出上古时期,人们养蚕织布,躬耕田园,那种最原始也最美好的男耕女织的画面。万亩青青桑园,着彩衣的女子穿梭其中,采桑摘果,该是一道多美的风景!在这里,没有看到蚕儿,蚕儿早已经结茧抽丝。记得小时候妈妈教我做针线,用的就是细长光洁白皙的蚕丝,那是我最早接触到的蚕丝。外婆家养蚕,但我没有见过。丝线盘成盘子,我不知道抽丝剥茧是怎样疼痛的一个过程,蚕丝的柔韧和手感却一直留在记忆里。在杭州的丝绸博物馆里,我见过大量的蚕茧,被存储在博物馆玻璃柜子里。一只只小小的蚕宝宝,啃噬桑叶长得白白胖胖,然后,开始吐丝,作茧自缚,用一根根雪白的丝将自己的身体包裹其中,吐完最后一根丝,让自己的生命化成美人香颈上的丝巾,获得永存。“春蚕到死丝方尽”,多么的执着!多么坚定的信仰!在厂房,有一刹那的恍惚,仿佛可以听见万万千千只蚕儿在啃噬桑叶,窸窸窣窣的声音,就像是高山上的流云,暗夜里的月光曲。没有看到蚕儿,但吃到了桑杏儿。紫色的风干的桑杏堆了一大袋子。咬一口,酸酸甜甜。阳光抽干了桑杏身体里的水分,留下了独特的味道,用来酿酒。我不太明白“三斤桑杏一斤酒”的酿制方法,对这种初见规模的“生产链”还是充满了期待。留在舌尖上的甜,留在唇齿间的紫,成了日后回味的余韵。大片的桑树,有着好看的姿容。不是扶摇直上的挺立,而是打叉修枝以后的枝繁叶茂,一簇簇,就是一道独特的风景。这里,真是一个充满期待、想象和向往的地方。而云台的厚重就在于“白马关”。一道关,走过了千年的岁月,承载了历史的风雨,记载着云台这座小镇的风云变幻。据说民国14年(年)白马关才改名为云台。之前,这个地方一直都叫白马关,白马关是云台的乳名,是云台的魂。自从有了“康县”之名,县治就设在白马关。站在白马关下,抬头望去,一座拱形的门洞上是青瓦红门的城楼。天下的关,都凝聚了人类的智慧,有登高望远,传递军情,防御外敌入侵的作用。当年因何种原因修筑白马关,白马关经过怎样的动乱和纷争,我无从知晓。触摸着墙体一侧粗粝的石头,触摸着存活下来的历史,似乎从一段历史的硝烟中走来。“白马关古城建于清光绪三年(年),城垣全为石头垒砌,周长丈,高1.9丈,宽1.2丈,有炮台4座,垛墙个。东西各修建门楼一座。东为“建光门”,西为“永安门”(现已毁)。”这是我打开百度输入“白马关”搜索到的词条。那么我们所在的就是东城门了。夕阳的余晖缓缓地洒在城楼上,城楼像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静静地望着云台小镇,目光祥和。踩着宽大的石条砌成的台阶,拾级而上,站在城楼上,放眼望去,一面是云台镇鳞次栉比的高楼,一面是马莲河上屹立近千年的“中山桥”(中山桥建于年,桥高4.8米,宽4米,长12米。桥房雕梁画栋,色彩艳丽,为夏日乘凉歇息佳处)。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大浪淘沙留存下来的石关和木桥在无声的诉说着白马关的历史。让人心生敬畏。吕带林诗曰:“云台山下水滔滔,晚时斜阳气势豪。错落人烟迷古寺,苍茫林树拥兰皋。余光直射西秦远,暮色曾殷北斗高。遥望牧童牛背影,漫将短笛认仙萧。”虽然此刻听不见水声涛涛,听不见钟声洪亮,看不见牧童晚归,轻吟此诗,依旧十分应景。美丽的白马关古城载有光荣的革命史迹。年9月19日,中国工农红军右路纵队二军六师三个团,在师长贺炳炎、政委廖汉生率领下长征到达这里,国民党县大队和县政府官员弃城逃跑。红军一部在城内留驻一周,发动群众,开展宣传,建立了康县第一个红色革命政权—康县苏维埃临时政府,播下了红色的革命火种。古老的康县在沉睡中觉醒。一块红色的石碑上,记录了这段历史。云台,不光有毛娅山的伟岸,大水沟的灵秀,最主要的,是有一道关、一座桥的坚守!在云台,择一地,与君采桑耕田,如此,也好!2窑坪往事 窑坪,不过是大南峪所属的一个小村庄。写下这两个字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窑坪往事》。这本砖头一样厚重的书,“是首部描写丝绸之路西北茶马古道的长篇小说”,是康北汉子王凤文先生的大作。在这部小说里,我首次知道窑坪这个地名。《窑坪往事》在我的眼里就是窑坪的一个文化符号。在一个转载请注明原文网址:http://www.linxiazx.com/lxsjt/6747.html |
时间:2021/2/25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星汇城VS星樾middot山畔同根同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
- 热点内容
-
- 没有热点文章
- 推荐文章
-
- 没有推荐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