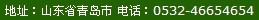|
大好人生有木有,没事跟着导航走! 谁来给临夏文学修一条铁路 文 石彦伟 绝不会有人否认,临夏州是个有魅力的地方。 但这魅力掩藏得着实深了一些。我到临夏去,要么走的是兰州,穿越狭长的城市找到客运南站,挤上大巴颠簸两个多小时才到临夏市区;要么就走大河家,从循化沿着黄河峭壁,七扭八拐,险象丛生。等终于进了临夏,遍览八坊,卧谈广河,走东乡大山,访拱北高人,最后再往朋友的大炕上一坐,喷香的手抓端上来,一切奔波都觉值得。只是慨叹,全国人民都在奔小康,为何不能给我们的临夏修通一条铁路,这样出出进进的,该增添多少便利!朋友笑说,快了快了,听说再有三年,火车就通了。 一条与时代同步的铁路,并不只为节省些时间和气力,它所联通着的,是大山外面那些辽阔的视野、丰富的色彩、多元的声音,是临夏与世界情怀的畅通,境界的融通。想到张承志笔下《大河家》《北庄的雪景》里那么动人的临夏之魅,还只能靠有心人主动去访,尚未被更多人发觉与感动,不禁感到一丝遗憾。但与此同时,交通条件的一时局限,也为一方地域的文学书写打开着某种茁长的可能:既然去一次不容易,这么好的地方,先在文学作品里过把瘾总是可以的。的确,临夏之魅在很大程度上,迫切需要文学的援助。铁路可以三年以后才能修通,但先给临夏的文学修一条快速路,确是当务之急,众望所指。 收获与困境:临夏文学仍在老牛拉车 事实上,临夏本土的多民族文学创作,曾有过扎实勤勉的努力。新时期以来,以言之回族,就出现了周梦诗、李栋林、高志俊、陕海青、马琴妙、马萍、马国山、马国春等一批作家。东乡族的成绩似更突出一些,老中青几代优秀作家几乎都出自临夏,汪玉良、马自祥、汪玉祥、马如基等老作家从这里走向全国文坛;钟翔、冯岩、冯军、马自东、马进祥、陈于放等中年一代,正逢秋实年景;近年又发现了马伟海、马潇、周楚男、八羊沟等一些新人,朝气蓬勃,富于可塑潜质。作为国宝一样的人口较少民族——保安族,仅万余人口里,也出现了绽秀义、马少青、马学武、马祖伟、马沛霆等一支生力军。加之撒拉族的韩小平,藏族的何延华,汉族的王国虎、杜撰、何其刚、王维胜、吴正湖、徐光文等,一眼望去,临夏的多民族文学俨然还是颇繁盛的一派景象。 但既然爱一个地方,真诚的话却不能不讲。临夏文坛当前所面临的困境,于我看来,是远远大于其曾取得的收获的。这一来是民族作家人数还太稀疏,水准过于平乏,创作也多处于停滞期。有“中国小麦加”之誉的临夏是回族自治州,民俗醇厚,掌故森列,理当是回族文学的一方重镇,但临夏回族作家的影响多还仅限本土,即便只说回族文学这个小圈子,放在全国格局中也尚无一位堪入核心阵容。常态之下,民族地区的文学,就该是民族文学为主体(内蒙、西藏、广西、延边等都是例子),但在临夏,稍显活跃的作者却少见少数民族。例如某县文联搞了一次临夏文学论坛,参会代表除一位少数民族外,全是汉族作家,临夏文学几乎与汉族文学无异。这真是一个使人多少有些惊诧,甚或埋怨的现象了。不包庇地讲,作为回族重镇的临夏,在出作家、出作品这一层面上,非但没有闪现亮色,反而是有些拖回族文学的后腿了。东乡族的情况要好一些,汪玉良先生是一位大诗人,在少数民族文学界堪属元勋,马自祥、马如基、钟翔也都获过“骏马奖”,但须知,东乡族的聚居地域主要就是临夏,别的地方则少见。也就是说,不能仅看临夏出了这么多东乡族作家就盲目地感到振奋,而应清醒地看到,东乡族文学的集体动员也就仅有这么多,与这个口传文学兴盛、内在气质极其适合文学表达的民族应有的实绩相比,尚有太多空白需要填补。至若积石山区亦为数不少的撒拉族,则尚未出现一位真正意义的写作者,藏族、土族的情况也比较尴尬。 我感到的另一个症候是,临夏本土对作家的培养机制显得贫弱乏力。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大凡写出些响动的作家,多是年轻时就走出了临夏,在外地成长和发展起来的,譬如汪玉良、马自祥、冯岩,也譬如青年一代的了一容、何延华等;而留守于临夏本地的作家,则只能低头拉车,谁若在《飞天》以外的全国性刊物发上篇东西,那简直要成为圈子争相传阅的新闻,至于小大名旦之类的名刊,则几乎从未登陆。茅奖、鲁奖没有得过尚能理解,但作为民族地区,本土成长起来获得了“骏马奖”的,目前竟仅有一个钟翔。论及中国作协会员,现居临夏的,各民族都算上,也大概仅有一个钟翔。而这个“零”,也是年才刚刚刷新的。看看临夏本地的文学生态,没有公开出版的文学刊物,仅有一本内部发行的《河州》,其品相甚至不如一本中学文学社社刊;基本没有专门针对回族、东乡族、撒拉族、保安族等土著民族作家的扶持机制、常态的文学活动,对突出作者缺少重视和奖励。如客居广河的回族作家敏洮舟近一两年势头很猛,接连摘得《民族文学》年度奖、黄河文学奖、年度最佳华文散文奖,在散文界堪称一匹黑马,如在一个生态健康的地区,一定以此为幸,相关奖励推介早就敞开了,可是那敏洮舟在当地仍是过着衣食无靠、籍籍无名的生活;还有一个新冒头的农民诗人阿麦,当过保安、服务员,开过电器铺,摆过地摊,现在还在县城蹬三轮车。他没钱买电脑,每次到网吧才能发一些东西,经常只能在手机上写诗。但就是这些诗已陆续在《民族文学》这样的国刊成为亮点,编辑们戏说,这样的诗若是炒作炒作,没准就成了第二个余秀华。刊物自然没有这般无聊,但爱诗的阿麦毕竟还是三块钱一趟地做着他的脚夫,卖了大白菜马上就去新华书店买成书。叫他拿一万元出来自费出本诗集,那简直是遥不可及的奢望。民间女作者尕荷的小说,在新月文学奖拿了个一等奖,按说有好的培养机制,就能趁势往前走几步,但什么都没有,她仍只能两眼一抹黑地原地打转。保安族作家马学武,上过《诗刊》,读过鲁院,刘云山同志接见过,中国作协当成国宝一样请了又请,我们都以为他在本地要受到多好的待遇,可是当我在他大河家的黄泥小屋住了一次之后,就什么都明白了,到现在四十多岁的他还在西宁穿着一身保安服看大门,受有钱人的冷眼——那可是我们保安民族当下唯一进入主流创作平台的作家呀!再看我准备在《民族文学》推介的东乡族大学生马潇、周楚男,从民族的稀缺性来说,也是应该重点培养的好苗子,可是去当地文坛问一问,有谁在意过青年作者的成长与前途?青年没出路,中年不给力,老年已失语,这寥寥三笔,大抵正是临夏文学眼前面相的真实速写。 坐标维度:对比之下触目惊心 让我们把临夏放在更大的坐标系中,进行一番对比与观察。 先与它的友邻甘南藏族自治州比一比。从兰州去甘南必经临夏,至其州府合作也需五小时,但就是如此地理偏僻之地,甘南的文学景观却引来了不俗的瞩目:老作家丹真贡布、伊丹才让、益希卓玛、白英华乃称大家,新时期以来雷建政、李城、完玛央金、扎西东珠、张存学等健步活跃,上世纪90年代以降则又出现了以阿信、桑子、敏彦文、李志勇、陈拓、扎西才让、瘦水、杜曼·叶尔江、嘎代才让、王小忠、花盛等为代表的“甘南诗群”,另如严英秀、敏奇才、刚杰·索木东等人的小说也都是当前民族文学界的有生力量。醒目阵容必有坚实阵地,甘南一州即办有两份文学刊物,如《达赛尔》系公开出版的藏文刊物,《格桑花》虽属内刊,却办得有声有色。就在前阵子,该刊还因编发回族作家敏奇才的头题小辑,而向我约组专题评论。如是用心办刊,远不似内刊气象。州内还设立了“达赛尔文学奖”和“格桑花文学奖”,分别奖励藏汉双语创作,至若其他政府奖励、散落社团、文选编纂、研究风潮,则不胜枚举。甘南与临夏,同为甘肃省仅有的两个民族自治州,为何一个盛景如斯,一个却黯淡无光? 下一个坐标系是甘肃文坛。热热闹闹的“八骏”评了一代又二代,诗歌大省的美誉似已远播,但这样的繁华与谁有关我不得而知,反正与临夏从来无关。临夏的本土诗坛(不算青年时代即已出走的临夏籍诗人,如汪玉良),从未出现过哪怕一位能够响当当站起来的诗人。试问,一个包含着这般荒地的甘肃,能称一片茂林吗?在我看来,真正的诗歌大省不是出现了几个有影响的诗人,而是这里的人们能够普遍地、广泛地爱诗、读诗、写诗,把诗当做生活的一部分,去追求,去尊重。甘肃文坛的繁荣背后如果掩藏着临夏的缺席,那也是不诚实,不匹配,至少是不完整的。 我们再把临夏与其他回族自治地区比一比。言及宁夏,“西海固作家群”的涌现已成经典,这不必再说,只谈区内上下对底层作家的帮扶力度,那也是文坛佳话,多少作家被调入文化机构,使其得以安心创作,不再为生计所累。文学遇冷之期,宁夏的本土刊物《朔方》非但没有商业化,反而增加了专门发表回族文学的刊中刊《新月》,使回族文学多了一双明慧的眼眸。若说宁夏回族众多,我想临夏也未必就少多少;若说西海固出作家是因苦甲天下,我去了东乡大山,却发现了比沙沟缺水区还要贫瘠的境况。宁夏大学曾建有回族文学研究所,整理出版过多部回族民间文学史料,进行作家专题研究,编选全国性的回族文学选本。最近,宁夏又刚刚出版了四卷五册、长达万言的《中国回族文学通史》,填补了回族文学史论研究的空白。再言及与临夏并列的、全国仅有的两个回族自治州之二的昌吉,年即创办了文学刊物《博格达》,年改名为《新疆回族文学》,新世纪以后干脆更名《回族文学》,于边疆远地逐步扛起了回族文学的大旗,30余年来对培养全国回族作家功不可没,已成回族文学创作的核心阵地。全国回族作家笔会也是由昌吉于年始办,此后二三届曾由临夏和宁夏分别坐庄一次,到了第四届,无人再管,此时又是昌吉勇敢地担起责任,一办就办到现今的第九届,仅我所参与过的即有四届之多!不知同为回族自治地域的临夏,在两个兄弟地区的作为面前,是否检视过自己建州以来对回族文学的贡献,是否正视过自己在文化领域落实党的民族政策的实绩? 最后,让我们跳出回族,与其他民族地区比一比,那恐怕就更是不敢一比的。先不谈民族文化较为强势的蒙古族之于内蒙,藏族之于西藏、青海,维吾尔、哈萨克族之于新疆,朝鲜族之于延边,仅来看普米族、傈僳族、德昂族等人口较少民族作家之于云南,那也是从省上到县里,被当成眼睛一样去爱护,发现一个培养一个,出书给钱,得奖给钱,作协入会优先,开青创会优先,就说鲁院启动民族班,也是先把较少民族作家送上前。而深居临夏同为较少民族的东乡族、撒拉族、保安族、土族作家,他们好像从未得到过本地专门的扶持培养,他们要在文学之路上起步、成长,无疑要比其他兄弟民族付出更多艰辛,克服更多阻力。不消说,临夏多民族作家之落寞、之沉寂、之无人瞩目,在同类民族地区不说是独一无二的,起码也是世所罕见的。 失语症从何而起 临夏文学负担沉重,际遇堪忧,可悲的是,这样的大实话却从来没有人像《皇帝的新装》里的那个小屁孩一样童言无忌地说出。然而作为一名举意推动回族文学事业的志愿者,我想,既然临夏印着回族的胎记,沾着回族的光,我就无法觉得它与我无关,无法对它至少落后文坛十年的窘境无动于衷。 临夏文学,究竟缘何失语? 文学的式微,作家之责首当其冲。我与临夏的多民族作者交往甚多,也熟悉他们的心态,我总是隐隐感到,他们对自己所处的创作生态缺乏忧患意识与担当精神,仿佛文学只是自娱自乐,闲下来就写一点,出了一本书混进了文学圈子,或是以此为敲门砖做上了官,便不再提笔,把文学甩得远远的。如若建议他们勤劳一些,特别是多写一些本民族生活,为身后站立的群山背影说句话,也促进族际之间的情感交融,他们往往会说:“我们那个地方很敏感,写出来也发表不了”,却很少思考到底是环境的问题,还是自身创作能力的问题。他们对文学还缺乏一点虔诚,对读书还缺乏一点痴迷,对文化先进地区还缺乏一点学习或赶超的志向。也或许由于自身的懈怠,他们的写作者荣誉也未能在当地受到应有的尊敬,常常被商人鄙视,被民众漠视,被职权者讽刺为疯子。此其一。 其二,民众是文化立足的根本。河州是回商文化的代表地区,善于经商的传统使一个民族走向富裕,却也可能带来文化上的短视。一些穆斯林家庭认为,能赚点小钱过上好日子就行了,孩子能认识厕所,懂得大马路上不能撒尿的道理就行了,学上多了没用,大学生出来也不分配,不如初中毕业就早早辍学跟父亲去做生意,有的甚至只念到小学,这在山大根深的东乡县比较突出。还有的认为,学习汉文化有损教门,字未识完就送进经堂。通识的道理是,若一个地区的青少年不能更多地走进高等学府,不能走出大山去外面的世界闯一闯、望一望,不能养成全民阅读的好习惯——让这里长出文学的庄稼,显然是奢侈的。 教育是使一个民族变得有教养的根本途径,如果学校教育受到阻碍,而传统的家庭教育,特别是宗教教育又因各种原因未能实际地发挥效能的话,一个地方的民众就可能发生道德滑坡,就可能出现守在路口收黑心钱、专宰外乡人的出租司机,就可能出现闻名南国的毒贩,就可能使一个地域的整体气质、对外形象受损,以致出现这里的人们想在中途搭上长途汽车,口音一露却被拒载的情况。贫瘠的道德沙漠,失约的社会伦理,归根结底是因为心灵的枯燥,是因为物欲强暴了理想,实用挤占了信仰。如果一方百姓、寺坊民众,能够在重视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宗教教育的同时,也把向善向美的文学作为改造精神世界的武器,让人们的心中多一些爱的典型、多一些人格巨人的形象,多一些寒风中升起的火炉,堕落时伸出的手臂,那么,古老的美德终会归来,人们的心灵终会强大。 其三,民族地区的文化职能部门都是清水衙门,普遍资金短缺,似也情有可原。但我们也看到,很多县一级的民族地区,却通过国家级文学刊物,与全国文学界保持着密切往来,文学活动十分频繁,所谓“小地方大视野”。它们也可能是经济欠发达地区,但政府的财政拨款有这个胆识和眼光,更多地向文化事业倾斜。这一定是当地文化部门与政府主动沟通、争取支持,并善于利用企业资源、外联协作的结果。坐等救济,明哲保身,那自然只能是形同虚设,毫无作为。而这样的地区,往往又有着通病,就是把“不作为”当成颠扑不破的晋升之道,偏偏要把那些出头做事的人逼成惊弓之鸟、万矢之的,仿佛他们打破了死水的平衡是多么罪大恶极。 另一个层面,是如何对待民族文化的问题。当前形势下,民族问题已是焦点问题,民族地区的政府特别是文化部门,是应该本着服务于少数民族群众精神需求的宗旨,为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扬多作助推,使其正能量得以传播,还是反视其为雷区,种种设障,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安安稳稳退休比什么都强。甚至于,别的民族地区争着抢着与一些国刊合作,接连举办作家培训班、改稿班、采风笔会、颁奖活动,而到了这个地区,却总觉得这些常态健康的文学活动也能影响安定团结大局,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一纸批文下来:“不办为好!”最悲哀的是,这样的批文往往正是出自民族干部的笔下。他们上边的一把手往往是汉族老大哥,为了不给自己的升迁造成不利因素,他们宁愿舍弃民族利益,主动选择沉默。可事实上,老大哥未必希望如此,我们的党也绝不会希望如此。 既然文学活动“不办为好”,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国家对民族地区的巨额财政拨款都流向了何处? 这两年的临夏,常能看到拔地而起的高层建筑,走近才知,三十几层的楼房却常常皆是空房,四五千元的房价老百姓还是买不起,而一边是房地产虚空易碎的泡沫经济,另一边,谈及图书馆、文化馆、剧场影院建设却总喊囊中羞涩。再如,当前“清真”二字已成国际经贸的一张名片,与清真沾边的地方政府花上几千万办一次清真食品展览会,把外国客商请进来,把国家投资要过来,是颇长面子又得实惠的好事。殊不知,那电视镜头里如雪片般翻飞的合同书背后,却是展会组织者找来大学生扮演成外地客商,与本土厂家签约,让全国人民都看到这里的黎明好热闹。镜头一收,一切归零,该萧条的萧条,该亏损的亏损。几千万玩一场化装舞会,无人觉得奢侈,可是花几万元给作家出本书,有人就开始苦穷了。 让临夏放缓脚步,寻找那片刻的静谧和真诚吧。 让临夏把烧下的钱留出那么万分之一,给牛车般踽踽蜗行的文学修起一条铁路,一条通往世道人心、直抵道德高地的铁路吧。 魅力临夏:呼唤与担当 终于谈到了这次“魅力临夏”散文诗歌大奖赛。如果这才是本文的主题,我并不以为前面所谈的一切都是跑题,恰恰,对临夏文坛种种症结的剖析与批评,正是我们真正认识“魅力临夏”珍贵意义的充分条件。从表面上看,这只是一次文学圈子的征文活动,或许在其他文学繁荣的地区,此类征文早已习以为常,然而,在了解临夏文坛历史与现状的知情者看来,在真正懂临夏、爱临夏、想为临夏的文化繁荣做出一点贡献的人们看来,这却是一件具有开拓意义和广泛影响的大事。它是历史上第一次由临夏本土有识之士自觉发起的、由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中国散文学会和中国诗歌学会等中国作协主管的三大国字头文学组织,联合了临夏州民委共同主办的一次文学赛事,是大山深处的临夏向世界发出的一个强烈讯号:“我们渴望表达,渴望表达自我,渴望被他者表达。”也是改造临夏文坛死水般沉闷闭塞之盘面,激活自上世纪80年代以后再未出现过的创作高潮的有眼光、有担当、有实效的力举。 在我看来,它至少引领了这样两股潮流:首先是沉默的临夏人,开始拿起笔来,表述自己渐行失落的“乡愁”。作为这次赛事的筹办人与评审之一,我可以负责地说,所有获奖作品的评选皆是唯看品质,基本没有考虑地域平衡、民族照顾。在9部诗歌获奖作品中,我欣喜地看到唯一来自回族的阿麦榜上有名(这组诗曾受到诗歌组评审、时任中国诗歌学会常务副会长的著名诗人李小雨老师的赞赏,而今李老师已离开我们,借此文谨向她致以深切怀念)。阿麦在《太子寺》中写到了“打马经过洮河”后,所见的水家清真寺:“大殿穹顶的弦月从不沉落/戴白帽穿青衣的男人们行走在暮色中/行走在寺院里——/阿訇颂经领拜众人跟着礼拜/动作整齐”,如若说这只是任何穆斯林聚居地域惯见的场景,那么诗歌第二节则融合了诗人独异的情感体验:“脸色凝重/仿佛每个人长着相同的脸/每个人都是天使/或者孩子”。这“相同的脸”,实则正是信仰者共通的思想彼岸,那是在精神圣域中沐浴的人们都能体会的神圣时刻:“此刻可以忽略许多事/譬如仇恨毒计穿过身体的蟒蛇”。这是临夏本土回族诗人对民族精神的一次别致的意会与开掘。 敏洮舟的散文《方寸间的大临夏》虽未能获得要奖,但其文印象深挚。作者选取了三个与临夏有关的名词:一条河流(即大夏河)、一座园子(即东公馆)、一所学校(即广河阿校),没有囿于惯常的地理书写,而是由地理而及人文,由状貌而涉魂魄,节制地提炼出临夏的风神。比如他感到大夏河“默默流出,纵贯两地,滋养了不同的土壤,也浸润了各自的信仰”,也感到广河阿校强健的读书声潮里,“奔腾着一个民族的寄托”。读敏洮舟的散文,我感到,唯大爱之襟怀、大世界之视野,方能看出脚下土地熟悉意象之外的人类价值。于是,方寸间的临夏,在他的笔下就这样开阔了起来,深刻了起来。同为回族的陕海青,在散文《东乡水窖》中,写到一个叫“考勤”的深山缺水村庄,“收集的窖水不是庭院地面的雨水,而是高洁的屋顶溜檐水”,由此感到了水的洁净、心的洁净。这并不是一个新颖的角度,在张承志90年代中叶以来所倡“清洁的精神”系列散作中,如是情节比比皆是,但我们经由张文了解的“洗心”传统更多发生在西海固大地,而同为信仰重镇的临夏东乡却疏于描述。从这个意义上看,陕海青的记录与发现,或可理解为信仰着的临夏文人表达意识的一种觉醒。 作为临夏特有的土著民族,几位东乡族、保安族作家的本土叙事亦值得治疗白癜风最好的药北京治疗白癜风比较好医院
|
当前位置: 临夏市 >思考谁来给临夏文学修一条铁路
时间:2018/3/29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工作动态安家坡乡中寨村开展社长选举工
- 下一篇文章: 临夏现代职业学院教育系2018届毕业生美
- 热点内容
-
- 没有热点文章
- 推荐文章
-
- 没有推荐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