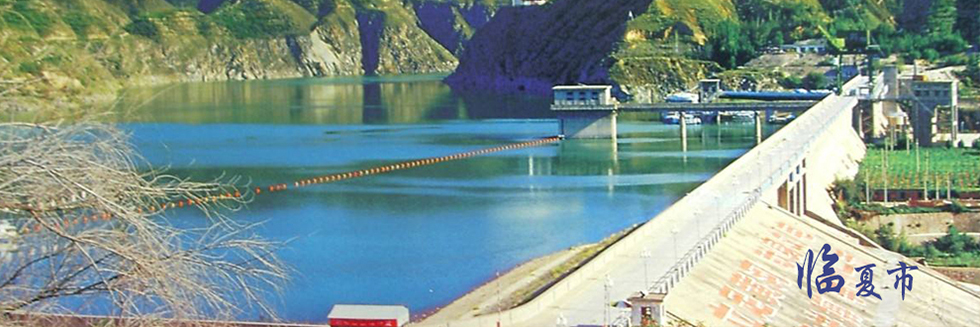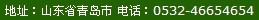|
内容摘要:伊斯兰教法中国化的本土经验可概括为“教法随国论”即教法随顺国法。所谓“随顺”意为“教随人定,法顺时行”。本文通过六个问题予以探讨:一、何谓“教法随顺国法”,二、如何理解“国法与教法之关系”,三、中国社会是否存在国法与教法之争,四、“教法随顺国法”如何理顺中国社会的政治权威与宗教权威之关系,五、“教法随顺国法”如何整合现代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与宗教认同,六、如何以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教法随国论”化解宗教极端主义的“教法建国论”。最后,“教法随国论”可总结为以下七个要点:“随顺国法论”“教随人定论”“法顺时行论”“信仰在地论”“政教互动论”“认同统一论”以及“多元共体论”。“教法随国论”的本土经验亦具有普遍意义,揭示了在非伊斯兰的政治实体中,伊斯兰教法如何随顺适应社会的问题。在长达千年的伊斯兰教法中国化进程中,形成了以教辅政的传统。历史上教法曾以习惯法形式为国家接纳,并在穆斯林群体内部发挥作用,从社会层面而非政治层面参与社会关系协调与秩序构建。这对于界定现代民族国家中伊斯兰教与国家关系,乃至伊斯兰教的现代转型等问题都是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具有普遍性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伊斯兰教教法国法随顺中国化 作者简介:李林,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伊斯兰教研究室主任。 本文的关键词为何是“伊斯兰教法”而非“伊斯兰教规”?对伊斯兰教而言,“教法”并非等于“清规戒律”,而是相当于宗教本身,故有“教即法,法即教”之谓。汉文译著家刘智有言:“道非教不明,教非法不立”。[1]就宗教本旨而论,此“法”非“国法”之法,乃教化之法、修持之道,属世界宗教典型范式之一,如犹太教亦重律法。宗教有“法”,实非个案。佛有佛法,儒有礼法,道教亦有道法、雷法、斋醮之法。宗教之外,非法而有法(前谓法律,后谓法度),亦非罕见。皆知书法有法,亦闻历法之法。故言,宗教之内,无须“见法色变”,而应细究其详。 一、教随人定,法顺时行:何谓“教法随国论”?本文所谓“教法随国法”当作何解?《易·坤卦》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坤之性,乃顺也。王弼注曰:“地形不顺,其势顺。”地形有高低险峻之“不顺”,但其承天之势则可谓“顺”矣。[2]“穆斯林”(Muslim)一词的本意乃“顺从者”,即全心全意顺从真主之人,教义学家称之为“顺主顺圣者”。“伊斯兰”(Islam)是“穆斯林”的同根词,有“顺从”、“和平”之意。此“顺从”有两重含义,即天人两尽,顺圣归真。先贤刘智曾言,“穆民”(Mumin)乃天方人之美称,依伊斯兰传统可译作“信士”或“顺者”,按儒家习惯则可译为“君子”,皆不失其本意。[3]真穆民乃真君子,真信士即真顺者。顺主、顺圣、顺亲、顺君,等次不同,然随顺之势,则一以贯之。故言:“教法随国法”之“随”,非随从、从属之谓,乃“随顺”之谓也。一言以蔽之,即“教随人定,法顺时行”。 (一)初解“教随人定”“教法随顺国法”,着眼点不再是“国法”与“教法”这两个笼统概念,而是将注意力转移为更为具体的人身上——即中国穆斯林群体。服从国法,经训既有明令,亦是身处特定国家的穆斯林不可推卸之政治义务。 考察历史,伊斯兰教法在中国的定位,实则与穆斯林群体的地位息息相关。伊斯兰教法在中国经历了“由俗而制,由制而礼”的演变。唐宋时期,它是化外之民的“习俗”;蒙元时期,它是管理穆斯林臣民的一套“通制”;明清以来,它是作为与儒家之礼相通的“礼法”。进入现代民族国家时期,它逐渐发展为公民个人的宗教信仰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化传统与习惯。[4]这些变化与穆斯林从“化外之人”演变为“化内臣民”,乃至“国家公民”的历程相一致,可谓“教随人定”。 (二)次解“法顺时行”伊斯兰教倡“中道”,儒家重“中庸”,皆尚中。伊斯兰教之中道,拟自空间。众人推坐于中间之人,即最具德行者。而儒家之中庸,乃时间之中,重在知几研时,察物入微。 《中庸》曰:“喜怒衰乐之末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此中庸之“中”,非物之中,乃时之中也,故谓“时中”:“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朱熹《中庸章句》解曰:“君子之所以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随时以处中。”[5]故曰:中与时相连。 《易·贲卦》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干宝注曰:“四时之变,悬乎日月。圣人之化,成乎文章。”[6]日月相推,寒暑相移,则生昼夜四时之变。天地有四时之变,人世则有兴衰往复。故须“观日月而要其会通,观文明而化成天下。”王夫之论“时”曰:“太上治时,其次先时,其次因时,最下亟违乎时……治时者,时然而弗然,消息乎己以匡时者也;先时者,时将然而导之,先时之所宗者也;因时者,时然而不得不然,从乎时以自免,而亦免亦。”[7]故须朗然玄照,鉴于未形。故曰:时与几相连。 《易·系辞上》云:“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易·系辞下》云:“几者,动之微,吉之先也。”唯有通其变,极其数,方能开物成务,由微知著。明清穆斯林学者在迻译教法典籍时,非通篇皆译,而是审慎选择,有所译,有所不译。主动回避了有悖礼法、不符国情的内容。刘智撰写《天方典礼》,唯论天道五功,人伦五典,而舍刑罚、圣战、税制、叛教者等篇不论,可谓知几矣,得乎中庸之道。 二、从教化到教法:如何理解“国法”与“教法”关系?卓新平提出,政治与宗教的关系大致可以归纳为:“政教合一”、“政教协约”、“政教分离”等模式,中国传统的政教关系比较特殊,可称之为“政主教从”,即宗教从属于国家,服从当权者的管理。[8]葛兆光较早引入福柯的“权力”与“知识”理论来分析中国政教关系,他的研究从“权力”与“知识”博弈的视角,将宗教与政治的关系解读为:屈服、抗衡与回避三种。[9] 这些研究表明,宗教与政治并非两个毫无交集的空洞概念。现实中,往往是政中有教,教中含政。两者多层面、多角度相互参与和介入。只有极端特殊的条件下即抽象空间,当两者被“化约”和“固化”为某种固定概念时,才被“压缩”为两个截然不同之物。如此一来。其关系自然逃不出形式逻辑的既定框架,只能如幽灵般徘徊于虚拟空间,其关系只能是:或矛盾,或一致;或平行,或交叉。当代人士热衷讨论的“国法与教法之争”,实则是望文生义,将虚作实,相当程度上来自语言和概念的误导。 在与伊斯兰教初识的“元始期”,伊斯兰教法一度被混淆为大食之国家法度。唐代杜环于《经行记》中,曾将伊斯兰教之规矩称为“大食法”。《经行记》一书已佚,现存文字见于《通典》: 诸国陆行之所经也,胡则一种,法有数般。有大食法,有大秦法,有寻寻法。……其大食法者,以弟子亲戚而作判典,纵有微过,不至相累。不食猪、狗、驴、马等肉,不拜国王、父母之尊,不信鬼神,祀天而已。其俗每七日一假,不买卖,不出纳,唯饮酒谑浪终日。[10] 不过,到了南宋,赵汝适撰写《诸蕃志》时,因接触日久,已知伊斯兰教并非“国家法度”,而是与佛教相类的“教度”。乃以佛教比附,不再称“大食法”,而改称“大食教度”: 王乃佛麻霞勿直下子孙……七日一次削发、剪爪甲,一日五次礼拜天,遵大食教度。以佛之子孙,故诸国归敬焉。[11] 明代以后陆续出现了“回回教门”、“天方教”、“清真教”等称呼。说明国人对对伊斯兰教的认识基本定型,视之为“教门、教化”,而不再笼统地之称为“法”。 《韩非子·内储说下》云:“大臣贵重……下乱国法,上以劫主”[12],这里的“国法”显然指国家制度与法令,与后来在帝国时期被称为“律”的成文法[13],有所区别。无论是作为传统帝国之“国”,还是现代民族国家之“国”,“国法”显然以作为政治实体的国家为前提,而“教法”乃真主之大道、天启的律法,两者在法律渊源上存在根本差异。此外,两者拥有各自发展脉络与历史轨迹,产生交错、会通之节点,只能存在于具体的律例和案例中。因此,国法与教法的关系,必须具体化,就事论事;而不能抽象化,将虚作实。如此方能成立,方有意义。 现代世界,为何有“教法与国法相争”的误读?根本原因在于,出现了“教法国法化”的曲解。“教法国法化”源于西方世界将伊斯兰教法解读为一种法律体系,即“教法法律化”。而现代伊斯兰世界,个别国家或政权按照现代民族国家的模式,重新阐释伊斯兰教法,将其作为国家合法性和强制力的来源,恰好为这一误读提供了“活生生”范例,似乎令人不得不信。反观中国,近代以来,西风东渐,礼治衰落,法治兴起。法律化的理解占据上风,逐渐影响了中国社会对于伊斯兰教法的认知,伊斯兰教法逐渐被视为一种可以与国家平行的法律和制度体系,甚至有取代国家法律和社会制度的危险。然而,如果回到中国传统社会,不难发现,根源于宗教的伊斯兰教法,乃是一套与儒家之礼相通的“礼法”。如此一来,所谓教法与国法相争的“危殆”是否还能成立呢?倘若教法恢复其“礼法面目”,则与国法势必不在同一层面,那么,两者又如何能够“相争”呢? 三、谈文化与论法律:中国社会是否存在“国法与教法之争”?“国法与教法关系”的演变历程足以说明,中国社会总体上从未出现“教法大于国法”或“教法与国法争权”之乱象。两者从来都不构成两种司法体系之间的平行或对立关系,更多是前者对后者主动吸纳,作为补充。对其关系的理解,不应被“化约论”和“本质化”的曲解所误导。而应认识到,两者关系,只有置于特定语境下、针对具体问题方能成立。 年出版的《中国与伊斯兰:先知、政党与法律》(ChinaandIslam:TheProphet,theParty,andIslam)一书中,作者尹孟修(MatthewS.Erie)在穆斯林聚居的甘肃临夏发现,所谓伊斯兰教法(IslamicLaw)与国家法律(StateLaw)不能相容的说法,并非事实。[14]这两种法律在现实生活中可以并存,一为国家法律,一为民族习惯,主次分明。颇具意味的是,在民间层面融合两种法律文化,沟通不同族群的共同基础,却是传统礼法所强调的道德教化。 所谓“教法大于国法”的说法,实则可细分为“教法大于国法”“教法多于国法”“教法先于国法”等三种类型。 (1)“教法大于国法”:即认为伊斯兰教是普世性宗教,不限于一国一隅,而“国法”即某个国家的法律制度乃至公序良俗,仅限于特定的国家和地区,实施范围相对有限。可谓从范围看,教法“大于”国法。 (2)“教法多于国法”:即申明教法在内涵上多于国法,因教法包含关于宗教信仰与功修等方面的规定,而现代国家的法律中通常不涉及此类内容。可谓从内容看,教法“多于”国法。 (3)“教法先于国法”:即主张对信仰者而言,教法所规定的宗教信仰先于国法。由顺从真主而忠于君主,此即先贤王岱舆所说“一元真忠”,顺主忠君并非二事,而是一以贯之。可谓从信仰看,教法“先于”国法。 值得注意的是,这三种认识,无一例外皆是从文化或信仰角度出发,并无从政治与法律角度出发声称“教法大于国法”或“教法高于国法”。显然,法律意义上的“教法大于国法”才是争论关键所在。可见,目前社会上对于中国是否存在“教法大于国法”的现象,虽争论激烈,聚讼纷纭,但实际多为鸡同鸭讲,各说各话。双方表面上治疗白癜风最好效果的药治疗皮肤病最好医院在哪里
|
当前位置: 临夏市 >李林丨ldquo教法随国论rdqu
时间:2020/1/4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观摩学习促发展,交流分享共成长临夏市第七
- 下一篇文章: 舌尖临夏特色美食厨艺大赛开赛
- 热点内容
-
- 没有热点文章
- 推荐文章
-
- 没有推荐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