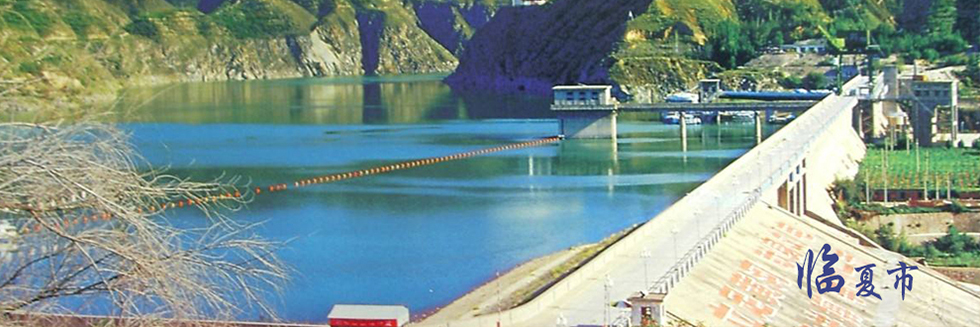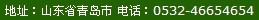|
精准治疗白癜风 https://m-mip.39.net/news/mipso_6185390.html (接上文:经堂教育漫谈(一);经堂教育漫谈(二);孔德军 经堂教育漫谈(三);孔德军 经堂教育漫谈(四);孔德军 经堂教育漫谈(五)) 我在镇上的寺里念经57天,吃油香花费了三分之一时间,送亡人不下20个,有时到其他村子去送,一去就是一天。至今支撑我一直要把经念到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和父亲在马受庆阿訇的清真寺门口一个月的苦苦等待。那时我腿部受重伤,行动不便,每天要流很多脓血,父亲则用自行车捎着我,每天去寺门口等待一位介绍人的消息。父亲因为害怕阿訇的威严而不敢自己去说,就委托阿訇的一位亲属到阿訇那里求情。我们就这样每天去寺门口等待,足足等了一个月,最终没有任何消息。后来得知,那位介绍人根本就没有跟阿訇讲过这件事情。于是父亲四处打听:难道除了这里,就没有其他地方教授词法吗?后来得知,临夏有位阿卜杜里俄福鲁阿訇,词法教得也相当好。我父亲在当地也算一个头面人物,尤其在商界受人尊重,为了我这不肖之子,却经受了这么多,那时我在心中默默地对父亲说:“阿大,您放心吧!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这份感情和期望,我一定会学好的。”我就这样到了临夏。在那里,我不但奠定了经学基础,更重要的是,我学会了怎样当一个穆斯林。安拉的事情充满了哲理。 见过马希庆阿訇的人都会被其高尚的人格魅力所打动,他平易近人,风趣幽默,做事雷厉风行,和我见过和想像中的任何一位阿訇截然不同。我见他的第一面,他首先向我道了色兰,让我大吃一惊。此前我还没有听说过一个阿訇会给满拉道色兰问好,或者一个长者给一个晚辈说色兰。由于写作和教学忙,他走路总是行色匆匆,给和他一起走路的人以小跑的感觉。今天,当我自己做一些文字工作时,才对他那时的情况有所感悟。当时堡子寺生活非常艰苦,满拉们每周四下午改善一次生活。所谓“改善”就是买两斤肉,让我们七十多个满拉享用。因为我来自“城里”,又是温存鏊阿爷(他是一个土族穆斯林,家景贫寒,青年时进教,是一个非常虔诚的老人。在他的带动他,他们家族上百名土族人归信伊斯兰。宗教改革中受尽了迫害和折磨,经受了巨大的考验,但他一直坚持自己的信仰。他以忠实可信而闻名遐迩,当地有钱的人喜欢把财产交给他保管,据我父亲讲:他的一个朋友年轻时不走正路,归真前将所有财产交给这位老人保管,并写下遗嘱:“如果儿子以后念成阿訇,就把财产交给儿子,否则就将把所有遗产送给清真寺。”后来那个儿子成为了一位阿訇。)介绍的,所以受到阿訇的格外关照,经常让我吃他的“阿訇饭”。“阿訇饭”是堡子村村民每晚给阿訇送来的饭,比满拉饭要好一些,但我基本上在其中没有看到过肉。有天晚上几个满拉煮了点羊骨,请阿訇来吃,期间有人开玩笑说:“我们在这里念了几年经,还不知道阿訇爷家的门朝哪开。”(意为阿訇没有请他吃过饭),没想到阿訇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是啊,我辛辛苦苦教了你们这么多年,你们连寒舍的门口都没有来过。”阿訇的机智幽默是非常出名的,有次讲《圣学复苏》时讲到穆民(对人)的好猜测,伪信士的歹猜测,阿訇举例说:“伪信士们看到阿訇经过电影院门口,就会造谣说:‘阿訇看电影去了!’”这时有个满拉举手说:“阿訇爷啊!如果发现阿訇在电影院呢?”阿訇立即回答说:“穆民就会想:‘阿訇爷来抓满拉了!’”阿訇留给我最难忘的一句话就是:“你为安拉考虑,安拉会为你考虑的。比如我,本来生活艰苦,现在情况就很好。”我知道阿訇一生非常清贫,那年他家的房子实在不能住了,就鼓着劲盖了两层小楼房,临夏的一些人开始说话了:“连阿卜杜里俄福鲁阿訇都盖了新房子。”我从来没有听过他说过脏话,这似乎是临夏地区许多阿訇的传统,有次一个满拉犯了件错误,阿訇非常生气,一时控制不住情绪,骂了句“坏孙!”满拉们从没有见阿訇这样生气过,一时鸦雀无声,没有想到阿訇自己却羞红了脸。穆圣(愿主福安之)说:“知耻是信仰的一部分。”主啊,在那一刻,我在阿訇的脸上看到了正信的光明。大西关的阿卜杜阿訇也是如此,从来不骂学生,但他的学生品德良好,学生们犯错误时他就咳嗽,一听到咳嗽声,犯错误的学生就会觉得非常愧疚。我想,这应该是经堂遗风。阿訇的大部分时间估计都用到了写作和教学上,他的房中总是铺满纸张,飘荡着浓浓的油墨味。这也是他一生最大的乐趣,他在归真前曾对我的师兄说,他在韩家寺开学期满后,要回到堡子寺继续教学。但没有想到他最终病倒在讲台上,从此再也没有站起来。阿訇的讲经方法也是别具一格,他讲有些经典时用传统的经堂语,讲另一些经典时则用“现代语”。他的经堂语如我前面所说:干净利落,层次分明,语法关系清晰,对句中的每个单词只讲一遍,这可以说是他和王永贤阿訇的“绝招”,也应该是经堂莱夫兹派最正宗的讲经方法(这种方法值得研究和发扬,此处不便举例说明。如果安拉赐我机遇,我想给满拉们写一本《教堂语教材》)。除他二人之外,马长庆阿訇讲经虽然也很优秀,但还是无法完全做到每个单词只讲一遍。王永贤阿訇告诉我:“这就是我从我的吾斯塌兹老人家(井口四师傅)那里接受到的真正的经堂语”。在清真寺里最早开设《在古兰的荫凉下》课程的估计是大祁寺的王孙迪格阿訇、时任韩家寺教长的上海阿訇和马希庆阿訇,但将这门课程一直开下去的则是马希庆阿訇,其他二位阿訇因为种种原因停止开这门课程后,马希庆阿訇则一反常态,改用现代语讲这门经。(王孙迪是一位品德非常高尚的阿訇,他讲瓦尔兹时非常严厉,对任何人都不留情。我旅居兰州那年,他老人家曾专程从临夏来看望我,对我寄予厚望,鼓励我翻译《在古兰的荫凉下》,我则忙于读研和和其他事情而未能从命。祈求安拉襄助这位老人!)后来我到广河听张维真老师讲这门课时,他见我对此经典非常熟悉,感到纳闷不可理解,以为我是哪里的“卧底”,对我的身份表示怀疑,据他后来讲:“当时我想不到还有哪个地方开设这门课程,阿语学校中不可能有你这样的人,有的话我一定会了解到的……除了哪个大学里接受过专门培训的人外,不会有任何一个满拉对这本经典如此熟悉。” 前面我们谈到马希庆阿訇的身教和言教,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九十年代初期,清真寺的教育是非常难搞的,在教育上革新的阿訇最起码要面临两方面的压力:一是满拉的综合素质,据我掌握的情况来看,那时寺里的满拉高中毕业的不到1%,如果哪个寺里有个“大学生满拉”,估计全城或全地区的人都会知道的。初中毕业生估计不到5%。大部分满拉是小学毕业甚至文盲,这在外语教学中简直是在创造一个奇迹。除了文化素质差外,另一个原因是道德素质差。我曾听“上海阿訇”在韩家寺讲:有个坊民带他的小儿子来找阿訇,希望收下这个孩子在寺里当满拉,此君毛遂自荐说:“阿訇爷啊!我的大儿子已经上班,二儿子在上大学,最让我头痛的这是这个小儿子,既不好好上学,也不好好做生意,家里实在管不了,就送来了,您一定要把他培养成一个人材呀!”此事绝非上海阿訇所虚构,就是九十年代初期甘宁青新地区清真寺生源的真实写照。 而八十年代教门刚刚开放时就不存在这种情况,当时虽然也有大批文盲进清真寺学习,但人们的教门意识端正,都愿意把家中最聪明最有前途的孩子送到寺里学习。可是八十年代初的情况正如前面所说——阿訇们基本上把当年所念的经忘完了,虽然一些阿訇的名气相当大,但其实际水平令人堪忧。那个时代许多阿訇的念经与其说是念,倒不如说是背,一生只念几本经,把这几本经的页码都背熟了,毫不夸张地说,许多阿訇可以不打开经典闭着眼睛讲。我曾发现这样一个令人惊讶的现象:一些阿訇只会讲他自己的经典,如果换一个版本,就不知应该从何讲起。把孩子送到这些阿訇那里去求学,其结果就可想而知了。说到这里,我的眼前经常会浮现出电影《火烧圆明圆》当中的一个情节:英勇无比的清兵高举大刀长矛冲向武装到牙齿的八国联军,然后在现代化大炮下一个个倒下去,最后全军覆没。八十年代初,仅我家族就有十几个人去念经,最后全部“倒”了下去,没有一个“活”着回来,最后不是经商,就是务农,有些既不会经商,也无处去务农,一生不知应该去做些什么。我的一位堂兄曾辞掉中学教师的职务去念经,最后还是没有成功。那真是一个悲壮的年代!在宗教开放后,只有个别精通语阿基础学、阅读视野开阔的阿訇没有忘记当年所学的知识。我们可以从青海地区公认的大阿訇马受庆的教学中对些有所认识。马受庆十八岁时就被马步芳任命为北关阿语学校副校长,可见其学问功底之扎实。但是宗教开放后他一直教小学——阿语词法和语法,很少讲经。一些群众不明白道理,问我:“人人都说受庆阿訇的尔林在青海属一属二,怎么不讲大经呢?”受庆老人家曾亲自对我们说明了这个原因:一,没有基础就不会有牢固的大厦(后面我将说明:讲经和学阿语是两个概念。阿语讲注实用,而讲经要慎之又慎。)。二,当时(在青海)没有人能教好这门课。这句话毫不夸张,是所有圈内人士公认的。三,他要在晚年把一生最宝贵的东西留给后人。这也使我最终明白了当年为什么井口四师傅不让马希庆讲经,而让他背词法,一背就是三十几遍。中国的现代阿拉伯语教学的历史不上百年,而作为有几百年历史的经堂教育,毕竟有其精华所在。今天,我们在评估和审视经堂教育时,应该如海市蜃楼网友所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不能全盘否定,自欺欺人。这也使我和世仁兄得出了一个相同的答案:为什么从整体上来看,中国留学生中念过经的人比没有念过经的人程度要好。当时教育革新的阿訇所面临的另一个压力就是文革时期遗留下来的坏毛口(习惯)--扣帽子,叫三抬,搞内部消耗。马志信阿訇、马希庆阿訇、甚至果园哈志的亲孙子长庆阿訇,都曾遭到一些宗教无赖的恶毒诬陷、诽谤和攻击,现在这种歪风邪气基本上在除青海之外的其他地方站不住脚了,在青海他们还在做最后的垂死的挣扎,把果园哈志所传播的好端端的“遵经革俗”运动搞了个乌烟瘴气,我甚至曾经奉功艾资哈尔大学留学回来的高材生金镖阿訇不要再和这些诽谤专业户计较下去,远走他乡,好好做一番事业,把一生最美好的时光和精力用到伊斯兰教育事业当中,没想到金兄气魄非凡,百折不挠,斗志昂扬,表示坚持到底,令人钦佩不已! 亲爱的朋友们,上面我罗罗嗦嗦讲了太多,大家的视觉一定疲惫不堪了,最近我自己的事情也是愈来愈多,所以我想在此做一总结,如果安拉赐我机遇,将其他话题留到专题讲座中吧,毕竟这是兰大在开会,而不是我的一言堂。我在其中则不幸扮演了历史上略懂修辞的铁匠散卡克,发表了太多牢骚。我的看法也不一定就是完全正确的。不过,正如我所说——为什么我的眼中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种教育爱的深沉——我是真诚的,也是痛苦的。如果要我说下去,估计最后要整理成一本书,但那又成了文字垃圾,白白站用小马的空间,没有实际意义。 在此,我要告诫大家的是:一,经堂必须更新观念,不但要培养阿訇或伊麻目,而且要培养出适应这个时代和社会的穆斯林,最起码要考虑这些人以后在社会上的立足之处。这需要从教学管理和课程设置方面做相当大的调整。并适当考虑是否送他们到国外深造,以便于以后他们考博士或进入国家教学和科研机构。 二,清真寺必须恢复其原有的根本职能——教学。所以,中国穆斯林传统上不把阿訇上任说成“上任”,而说“开学”。做到这一点,需要穆斯林群众认识到真正的教门是念、礼、课、斋、朝,是命人行善,止人作恶,搞好教育和宣传,把更多的人引向伊斯兰,而不是一家排一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请阿訇吃饭过乜提。过乜提如果影响到下一代人的宗教教育,则成了一件大罪。正如我们眼看一个人要掉进万丈深渊,不但不出手相救,而且还对他说:“我刚才打了一个喷嚏,你怎么不回答呀?回答喷嚏可是一件圣行!”伊麻目安萨里在其《圣学复苏》中对类似问题有相当多的论述,当代著名学者优素福格尔达微先生的《优先选择》中更有明确例举,不妨有时间去瞧一瞧。为了便于可爱的中国哈万提明白这个道理,我在此引用和“应答请教”一样重要的一件圣行——“回答喷嚏”作比喻。须知,如果一个阿訇没有时间讲经教学,而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过乜提,那么他的情况就无异于一个濒临万丈深渊的人。今天,某些地方的阿訇已经成为“过乜提”专业户,没有时间和精力讲经教学,而群众对此毫无知觉,一些群众甚至对阿訇的要求不再是宣传和教学,而是“是不是五番礼拜都在者麻提上”、“是不是谁家请教都能应答”。须知,后世的惩罚不光针对阿訇,还针对每一个哈万提。只顾自己一时痛快请阿訇吃饭,而对伊斯兰大局不理不睬的人,是最自私和可恨的人。 相关链接: 经堂教育漫谈(一) 经堂教育漫谈(二) 孔德军 经堂教育漫谈(三) 孔德军 经堂教育漫谈(四) 孔德军 经堂教育漫谈(五)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转载请注明原文网址:http://www.linxiazx.com/lxsrk/6333.html |
当前位置: 临夏市 >孔德军经堂教育漫谈六
时间:2020/11/19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临夏风光集萃二十一夏末的法台山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
- 热点内容
-
- 没有热点文章
- 推荐文章
-
- 没有推荐文章